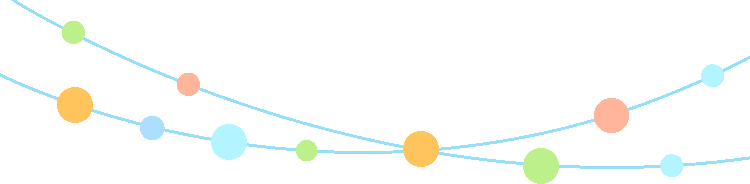九月的桂花落满阳台时,我发现女儿小棠的校服袖口总是卷到肘部。
她以前从不这样 —— 那个暑假还抱着吉他唱民谣的姑娘,上初中到现在不过3个月,就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
书包往沙发上一扔就钻进房间,晚饭时碗里的米饭总剩下大半。
“她又没吃多少。” 妻子林慧把空碗重重磕在灶台上,洗洁精泡沫溅到瓷砖上,
“每天除了锁门就是发呆,哪像个初中生?” 我捏着刚从医院取来的检查单,“中度抑郁” 四个字刺得眼睛生疼。
医生说青春期孩子敏感,建议药物配合心理疏导,我咬咬牙交了第一个疗程的费用。
接下来的半年,我带着小棠跑遍了城里的专科医院。
认知行为治疗室的沙发坐出了凹陷,中药汤熬得整个楼道都飘着苦味,连据说很灵的心理咨询师都换了三个。
银行卡的余额从五位数变成四位数,最后小棠依然抱着膝盖坐在飘窗上,看楼下的梧桐叶从绿变黄。
“爸,我不想去学校。” 她的声音像蒙着层砂纸,校服领口的扣子扣到最上面,把下巴埋得严严实实。
我蹲在她面前,看见她手腕上有几道浅浅的红痕,心脏像被老虎钳夹住:“咱们再换家医院好不好?北京的专家我都约好了。”
她摇摇头,把脸转向玻璃,映出我两鬓新添的白发。
那天林慧提前下班,撞见小棠把书包里的课本全倒在地上。
“你到底想干什么?” 她的声音在客厅里炸开,手里的帆布包甩在茶几上,水果滚得满地都是。
小棠没抬头,手指无意识地抠着地毯的线头。“花了八万块带你看病,你倒好,变本加厉地作!”
林慧的声音陡然拔高,我刚想拦,巴掌已经落在小棠脸上。
“啪” 的一声脆响,空气瞬间凝固。小棠的脸颊浮起五道红痕,她没哭,只是慢慢抬起头,眼神空得像口枯井。
林慧的手僵在半空,指尖微微发抖:“那么矫情干什么?我像你这么大时,早就下地挣工分了!”
我突然笑了,笑得肩膀直抖。
林慧愣住了,小棠也眨了眨眼。
他们大概忘了,上周去心理咨询时,咨询师反复说的那句话:“家庭系统里的压抑,往往会转化成孩子的自我攻击。”
我想起林慧总在饭桌上说 “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想起我逼着小棠报她不喜欢的奥数班,想起我们总在她关门后讨论 “她是不是在装病”。
这一巴掌,像根烧红的烙铁,烫穿了所有自欺欺人的伪装。
我扶着小棠的肩膀,她的身体还在发颤,却第一次没有推开我。“明天咱们不去医院了。”
我擦掉她嘴角的泪珠,声音出奇地平静,“去你外婆家摘橘子,你小时候最喜欢爬那棵老橘树。”
林慧站在原地,围裙上的油渍洇成了深色。
窗外的月光漫进来,照亮小棠脸上渐渐消退的红痕,也照亮了我们这个家早已千疮百孔的模样。
原来有些病,从来不是靠钱能治好的,它需要的不是药物和诊室,而是有人愿意蹲下来,听听那些藏在沉默里的呼救。
第二天清晨,小棠主动把校服袖口放了下来。
她站在玄关换鞋时,我看见她对着镜子扯了扯嘴角,虽然还是没笑,但那双蒙尘的眼睛里,总算透进了一丝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