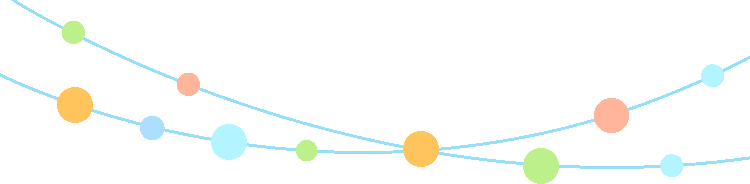傍晚时分,新三余村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们排成排,牵起手。在老师一声令下后,有的小朋友飞快地跑来,站在第一个,骄傲地昂起头,有的小朋友慢吞吞、行动迟缓,但也规规矩矩地把脚迈进白线以内。
如果不仔细看,难以发现有的小朋友手部无力,无法画出流畅的线条,有的小朋友总爱盯着一处发呆,总是慢半拍。其实,这里的每十个孩子中,至少有一个是身心障碍儿童。
融合教育(Inclusion),就是将身心障碍儿童和普通儿童放在同一间教室一起学习,让有特殊需要的儿童不被隔离在特殊学校,而是回归到正常的主流学习环境,接受无差别的正常教育。
被幼儿园拒收后
村里幼儿园的园长瞅了一眼,说,“你家这个发育太差了,我们不敢收”。
隔壁村幼儿园的园长皱着眉头,不太乐意继续谈下去。
镇子上的幼儿园说,等通知吧,但是电话再也没有打来。
残联七彩梦特殊幼儿园回复说春季不再招收新生了。
……
被幼儿园拒绝十五次后,澄宝的妈妈小付逐渐陷入了迷茫的惊惶之中。
“不看了吧,不收就在家里带带算了”。澄宝的爸爸想要放弃了,从孩子确诊以来,村里的流言,亲戚朋友的另眼相待,让夫妻俩几乎进入了一种习得性无助的心理状态。普通孩子必经的漫漫求学路,他们都无法踏出这艰难的第一步。
澄宝一晃快要五周岁了,仍然每天穿梭于各种康复机构之中,社交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难以正常融入集体,因此,小付打定主意要让孩子进入幼儿园,“但哪有幼儿园愿意接纳这样的孩子呢,我们找了那么多家,也没有人愿意收”。
图1 澄宝妈妈找幼儿园时做的笔记
她给当地教育局打过两通电话。
第一次,教育局回复说有一个公立幼儿园,让他们去试试。等了两年,终于开始招生了,但一家人去了以后才发现,公立幼儿园限制非常多,且只收了其他方面发育正常的听障儿童,根本不是所谓的融合,筛掉了澄宝。
第二次,小付打电话过去,非常气愤地说:“我等了两年,就等来了这么一个结果”。但教育局的回复是,当地确实是没有融合幼儿园,他们也没办法,毕竟幼儿园也不是义务教育。无奈,教育局“非义务教育”的回复像是彻底堵死了这条路。
图2 小付发表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号召大家搜索融合教育学校
无数次被拒绝、被劝退,似乎是每一位独症谱系障碍(以下简称孤独症)儿童的父母心中最酸涩却又最无可奈何的痛楚。
丞丞的妈妈小柴也同样遇到了这样的难题,她又接到了幼儿园打来的电话。
幼儿园老师说,丞丞在幼儿园一天都不吃一口东西、一点儿都不听话、情绪暴躁又易怒、上课到处跑根本坐不住……她听着老师絮絮叨叨地念着,无非是重复那些她听了不下数百次的抱怨。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太多太多次,最终,幼儿园给丞丞下了最后通牒,“把孩子接回去吧,我们实在是带不了了”。
无论是私立还是公立幼儿园,丞丞都没能待下去。小柴别无他法,只好带着孩子又一次踏上了荆棘丛生的求学路。
自从被冠上“父母”的称号后,困难接踵而至。然而,最难的,当属带着孩子迈出家门、拥抱社会的第一步。
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纪,孤独症儿童被社会无形地“隔离”开来了。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的《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中载明,孤独症是一类发生于儿童早期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以社交沟通障碍、行为重复刻板等为主要特征。
图3 《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中所载的筛查表
而幼儿园作为培养幼儿集体意识和社交能力的重要场所,孤独症儿童仿佛天生就被剥夺了上幼儿园的权利。
孤独症的阴影,同样笼罩了周婷婷的家庭。然而,对于本就担任幼儿园园长的她而言,这是挑战,也是人生路径转折的重要机遇。
在周婷婷的侄子两岁的时候,家人就发现了他和正常的孩子不太一样,把他带去医院,确诊了孤独症。接下来的日子,她的侄子和多数孤独症小朋友一样,被送去特殊教育机构进行干预,一去就是两年。
周婷婷的职业是教师,因此她深知儿童每一个阶段的教育重点。“进入幼儿教育领域后,我知道孤独症儿童需要去社交。那他的社交场是什么?是家庭、是社区,但大多时候是在幼儿园,他需要进幼儿园。但他那时候已经四岁了,又没有地方可去,我们非常非常着急”,周婷婷和家人急得团团转。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在央视财经《第一时间》节目里表示,当前,孤独症并没有药物治疗,主要的治疗方法只有康复训练,最佳时期为6岁前,因此,对儿童孤独症进行早期筛查和干预十分重要。在相同的病症情况下,在普通学校就读的孤独症儿童的情绪控制能力、社交能力、沟通表现都会好于在特殊学校中的孤独症儿童,且与融合教育时间呈正相关。
周婷婷找遍了所有能招收特殊孩子的融合园,但北京没有、东北老家也没有,甚至找遍了整个中国都没有,就算能接收,进去也是难上加难,入学名额供不应求,用她的话说“等个几年,根本排不上号儿,排到了也晚了”。
孤独症融入普通幼儿的最佳融合比例为1:10,也就是说,10个正常孩子(简称NT,neurotypical)孩子才能融合进一个孤独症儿童,因此,想入学,就不得不面对长达数年的排队等待。但周婷婷明白,孤独症儿童的最佳融合阶段为3–6岁,孩子等不起。
在这个过程中,她也接触到了一大批孤独症儿童家长,他们被普通幼儿园劝退、拒收,或隐藏孤独症病症入园,但入园后,孩子得不到有效引导,被老师冷眼相待,反而加重了情绪负担。
据中国残联最新发布的《中国残疾人普查报告》数据显示,孤独症患者已超1300万人,且以每年近20万人的速度增长,其发病率成为精神类残疾的首位。
对孩子来说,3–6岁,他们的大脑正在快速发育,在这一阶段,他们对社会的适应和接纳能力更为敏感,是孤独症儿童最黄金的融合阶段。然而,地区资源的不平衡、融合需求的紧迫性、幼儿园非义务教育的属性,三者相互交织,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坎。
约300万孤独症儿童融合需求的紧迫性与社会现实的极大缺失,构成了这个群体的核心问题。但是,如何让他们获得平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谁来引导他们融入集体,融合教育行业如何破局?
如潮水般汹涌而来的现实困境,对周婷婷来说,解决方法好像只剩下了一条路——没办法,只能自力更生,自己做。
摸着石头过河:新三余村里彻夜不灭的灯
这里离繁华的北京市区相去甚远,刚洗干净的粉红色床单就晾在街边,路牌的铁杆也生了锈。三轮车吐着尾气缓缓前行,各家的排气风扇挂在外壁上,轰隆隆地作响。
拐进路口,道路就显得平整很多,那是去幼儿园必经之路,也是家长们每天雷打不动、带着孩子通勤几十公里的目的地。
图4 新三余村幼儿园
新三余村,是一个位于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的城中村落。村内多为村民自建平房或二层小楼,但交通便利,秩序井然。这里坐落着大兴区唯一一家融合幼儿园——新三余村幼儿园,作为村级公办园,园子面积不大,但滑梯、障碍物、各类玩具一应俱全,墙上满满当当挂满了锦旗、小朋友们的画、一起做游戏的合影,看上去与普通幼儿园并无二致。
每到中午,就有坐在新三余村幼儿园门口的石墩上等待的家长,他们多数是上了年岁的老人,拿着印着迪士尼公主或奥特曼的保温杯,伸着脖子望着,等着中午接到孩子,下午再送他们去特教康复机构做干预。
时间飞逝,这已经是周婷婷做融合幼儿园的第七个年头。
周婷婷坐在监控室,看着来来去去的每一个都能叫上名的孩子,讲起她一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故事。
从高中老师,再到教初中、小学,最后又做了幼儿园园长,在教育的道路上,她仿佛一直在“开倒车”。
2002年本科毕业后,她去了青岛的一家民办学校做教师,但潮湿的气候让她的身体开始过敏,浑身上下起了荨麻疹,无奈之下,只好又回到北京攻读硕士学位,但研究生的学习年限拉长了她的求学之路,毕业后,因年龄限制,她还是错失了进入公立学校体制内的机会。于是,从2013年起,周婷婷来到新三余村,做起了普通的村办幼儿园。
2017年,面临侄子“无学可上、无处融合”的困境,她下定决心自己做融合教育,干脆把新三余村幼儿园改成了一家融合性质的幼儿园,重点招收孤独症孩子入学。目前,幼儿园里有二百六十多个孩子,有二十个左右的特殊孩子。
从自学ABA、BCBA课程、自考融合教师证开始,周婷婷在幼儿园里,点起了一盏“长明灯”。
年轻幼师们穿着统一的红黑色制服,头发松松地用鲨鱼夹夹起,认真而质朴,应对着孩子们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她们忙不迭地在园子走动着,准备手工课的玩具、在孩子们的书包里放好作业本、带领着孩子们吃饭睡觉,一刻不停歇。
将普通幼儿园变为融合,对于园长和老师而言,学习专业知识、获取上岗资质是第一道坎。
图5 新三余村幼儿园书架上摆满了融合教育的书籍
“我们培训了包括园长、美术老师、音乐老师等等所有的老师,进行了专业的训练,还要考融合教师证、考特教老师证”。周婷婷认为,如果老师没有经过培训,对特需儿童是一种剥削,对老师来说,这样的工作也是折磨。
自此,幼儿园里的“长明灯”越来越亮,彻夜不灭。
“刚开始接触融合的时候,真不想学,也很排斥”,萌萌老师在幼儿园大班做主班老师,学前教育专业出身的她,已经从事了五年的融合教育工作。谈起学习融合知识的那段日子,她用“熬人”二字来形容。
每天早晨7点开始上班,下午6点下班以后,所有老师需要继续在幼儿园里学习到晚上9点或10点。除此之外,还要考试,被特教老师带着练回合,等终于下班了,再一条条回家长消息。最后,上课、考试、考证、才能上岗。
“一开始觉得真带不了这种孩子,一整天的情绪可能都会被影响”,萌萌老师讲到,做融合老师需要一步一步来。刚开始,大家都很崩溃,但慢慢适应了之后,就互相鼓励,发现学的知识用到孩子身上有效果了,慢慢变好了,逐渐获得了正反馈。
新三余村幼儿园摸索出了一套融合园的师资配置机制,以班为单位,一个班配备主班老师、配班老师、保育老师,需要考融合资格证、特教资格证、教师资格证,只有证件齐全的老师才能成为主班老师。从种类上看,融合老师负责普通儿童与特需儿童的幼儿园课程、把控孩子的整体目标,特教老师负责训练特需儿童的行为、感统、言语表达等康复训练课程,影子老师则针对程度比较严重、无法融入集体环境的特需儿童,在其入园前期给予支持,随后便慢慢撤出。
小柴原本是一名幼儿教师,将患有孤独症的儿子丞丞送入新三余幼儿园后,她也投身其中,开始学习融合教育和特殊教育的专业知识,成为了一名融合教师。像小柴这样的人也在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幼师也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
孤独症儿童被称作星星的孩子,因为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像星星一样遥不可及。“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周婷婷走了七年。如今,这条路上那盏彻夜亮起的灯,让星星开始融光,也让遥不可及变得触手可及。
对于融合教育的初探,大多数人都如同周婷婷一样,起初是因为家人或身边亲近的人被诊断出孤独症,现实困境又使其所求无门,才决定以个人为单位,零散且缓慢地摸索着融合教育的道路。
彭帅臣也是其中一员。早年间,他在北京做影视制作工作,策划过总台春晚、《非常6+1》等知名节目,机缘巧合下,投资了家乡山西忻州的一家幼儿园。也许是命中注定,这个无意间投资的幼儿园,成为了他人生轨迹的重要拐点。
2015年,他一岁半的女儿被诊断出孤独症。一家人带着女儿辗转各地,巨大的经济压力使得彭帅臣于2019年回到了家乡忻州,将自己早年间投资的幼儿园转变为了融合园,走上了自立门户的道路。
将已有的幼儿园资源变“融合”,是探索融合园的重要路径。如果没有幼儿教育资源,又该如何起步?
安老师给出了另一种答案。2010年,学前教育专业刚毕业的她,实习时接触到了一个被诊断为精神一级残疾的孤独症儿童,好奇和善良驱使她更多地关注着这个从不张口说话的小男孩,随着感情的加深,她离开了幼儿园,成为了男孩如影随形的影子老师。
“没有地方收我们,没有幼儿园让影子老师陪读的先例”。安老师四处碰壁,屡屡被拒,“直到碰到了一位非常有情怀的园长,我们才终于安顿了下来”。
在这个过程中,她认识了大批同类型的家长,想让孩子接受特训以外的正常教育。于是,她开始寻求与普通幼儿园的合作,做成了第一个融合教育班,这一做,就是十三年。
如今,她成立了星愿融合机构,搭建起家长与幼儿园之间的桥梁,与四家普通幼儿园展开了合作。当孤独症儿童状态好的时候,就送他们到幼儿园进行融合,锻炼规则意识与社交能力,当他们状态较差时,则撤回机构,承接他们的情绪。
总的来说,融合幼儿园的入局形式较为多元,包括链接特需儿童与普通幼儿园的融合机构、普通幼儿园自我转型的融合园、依靠投资转型的融合园等等,形式多样,其中有私立园、也有公立园。除此之外,还有政府资助的残联幼儿园,部分招收孤独症儿童,然而,这些幼儿园对特殊幼儿的能力评估较为严格、门槛较高,且不算是完全意义上的“融合环境”,不被大多数家长所选择。
摸索融合,从“吃饭”开始
这些行业的初探者朝着未知的方向涉水淌河,逐渐走出星星融光的“经验式”道路。
图6 家长中午在门口接孩子,下午再把孩子从幼儿园送到康复机构
“他问我,‘老师,你怎么不去死?’,然后一口咬住了我的胳膊。”
“同一个问题,不断刻板地询问,比如喝水是什么?为什么要喝水?什么时候喝水呀?喝水之后干什么呀?”
“别的小朋友玩,他就呆呆地盯着转动的风扇,一动不动。”
想起作为融合老师的这几年,萌萌老师也有一把辛酸泪。
作为一种终身伴随的广泛性发育障碍,孤独症的核心障碍,便是社交障碍,没有特效药可治,只能通过长期系统的干预改善症状。
当面对孤独症儿童的刻板行为、或过激的情绪性动作时,融合老师逐渐摸索出一套专业的分解机制,能够有效引导其融入集体生活。
小到纠正“吃饭只吃糊状食物”“害怕冲厕所”,大到纠正骂人、打人、多动。融合的过程是细碎的、繁琐的,全天候的。
进入新三余村幼儿园,老师们发现,道道从不吃幼儿园的饭,只吃姥姥带来的泥状饭团,并且伴随着不小便、不喝水等刻板行为,难以融班。
于是,道道的融合之路,便从“吃饭”开始。一个困难出现了,融合老师便要去分解,这个困难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发生?应该怎么办?是什么因素让他感到不舒服了?分解之后,就降低目标,让他慢慢完成。
“经过目标降解,我们发现他不吃饭,是因为他只能吃糊状的食物”。萌萌老师回忆道,为了纠正这一行为,老师们把丁状的食物混到糊糊里,慢慢增加比例,从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三,再开始尝试混进大一点的片状食物。经过脱敏、差别强化等干预策略,道道开始一口一口张嘴吃下了幼儿园的饭菜。
图7 孤独症儿童丞丞正在学着自己吃饭
融合过程往往非常缓慢,比如,让安吉克服厕所冲水这件事,老师们就花费了差不多半个学期。老师们开展了无数个“对照实验”,终于发现了安吉不冲厕所的原因——害怕冲水声。
于是,从水滴声、到水流声、再到冲水声,老师们“逐个攻破”,最后安吉慢慢适应了这个声音,也终于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们一起自己去上厕所了。对于他来说,这是生活能够自理的重要一步。
孤独症儿童对细微事物的抗拒往往事出有因,不冲厕所,可能是源于“感到不卫生”“怕水”“怕冲水按钮”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融合老师要做的,就是找出这个具体而细微的原因,并给予帮助、纠正它。无数个涉及生活方方面面的行为被纠正后,真正的“融合”便形成了。
语言认识、运动、社交能力、班级融合能力,融合老师逐渐在幼儿园的场域内提升孩子们的能力,并慢慢撤出,减少他的的依赖性,再通过父母去泛化,使得他们也可以完成爸爸妈妈或者其他人的指令。
在这个过程中,当孤独症儿童无法表达自己的需求、情绪崩溃的时候,老师们可以将其带至小教室里进行安抚,并开展小班教学,从而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
图8 老师安抚着特需儿童(左)、为特需儿童准备的多功能教室(右)
除此之外,融合教育的另一的面是对普通孩子的教育。
融合教育需要秉持着“有教无类”的思想,让正常的孩子与有孤独症的孩子共享同一个课堂,让不同的孩子们都享受着同等的公平。
安老师讲到,幼儿园其实是最适合开展融合的地方,因为孩子们的心灵足够纯真和善良,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处在一个正在被塑造的阶段,因此,让孩子们意识到“特需儿童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更加需要他们的帮助”,是形成融合环境的重要因素。
图9 孤独症儿童和普通儿童一起做手工
手工课上,安吉可以正常地与同伴共同制作飞机模型,虽然有时慢吞吞、或者不小心撞到已经拼好的成果,但是小女孩也不恼,继续帮助安吉完成剩下的工作。
其他与孤独症儿童搭配成组的小朋友同样如此,他们似乎更加包容、温和,懂得如何帮助别人,这些离不开融合教育老师对普通孩子们的引导。他们一起课间活动、每月一起过幼儿园的专属生日会、一起上课、小组合作,成为彼此亲密的伙伴。
在这里,孤独症儿童不再被无形地隔离开来,找到了可以融入的栖身之所。
图10 孤独症儿童和正常儿童一起上课
图11 “生日会”统计表(左)、生日会(右)
融合幼儿园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与发展后,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体系和经验模式,但一些深层次的、普遍性的问题也逐渐浮现出来。这些困境源自何处?又将影响着融合教育行业走向何方?
融合路上接踵而至的困境
在融合教育的进程中,这些行业入局者的普遍性困境逐渐浮出水面,如影随形,贯穿始终。
首先便是降无可降的融合费用和经济压力。
小柴和丈夫在离幼儿园仅有两分钟路程的地方,租了一间仅有20平米左右的街边房。从幼儿园的后门出去,走两分钟土路就能到。门口是两排晾衣架,地上堆着快递盒、孩子的学步车、皮球,略显逼仄的里屋,放置着一张床和一些简易的家具。
“村里的房子一个月房租2000元,幼儿园的融合费用是6000元一个月,加上每天一节220元的一对一特教课,一个月需要花费一万到两万元左右”。在北京的城中村,小柴已经尽可能压缩了丞丞的融合费用以及一家人的生活成本。但谈起经济负担,她还是感到非常焦虑。
被经济压力压得喘不过气的不只小柴一人。山西忻州星星屿创始人彭帅臣之所以回到家乡自主创业,便是因为一线城市的费用太过高昂,他和妻子在女儿确诊后不久,就带她走遍了全国最好的机构,康复、房租、日常开销,一年下来高达二三十万。
安老师讲到,在北京,孤独症的特教康复机构的平均价格为两三万一个月,有些高端机构的价格更是高达十几万一个月。再加之同样动辄上万元的融合费用,“花钱如流水,这种家庭负担一般人难以承受”。
此外,由于孤独症儿童需要专人照顾,核心家庭中往往有一方“被捆绑在家中”,这导致家庭劳动力减少,收入减少。《中国孤独症及神经发育障碍人群家庭现状需求及支持资源情况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有4%的父亲和54%的母亲目前处在无业状态,年家庭收入损失6.7万元左右,无业状态并非几个月的短暂时性行为,而是数以年计(父亲33.7个月,母亲46.8个月)不能返回职场。
然而,这看似是一个无解的命题。
在新三余村幼儿园,孤独症等特需儿童每月最少需要一万元左右的融合费用,而这已经是尽可能降低家长经济负担的结果。
周婷婷掰着指头,算了一笔账。在北京,一个本科毕业生的基本工资预期是5000元起,社保和公积金3000元,再加上培训中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去学习融合教育和特殊教育方面的专业知识,一个融合老师的工资最低一万元。对于孤独症儿童而言,他们通常需要一位融合老师、一位特教老师、一位保育老师,甚至情况严重的还可能需要配备影子老师。从这个角度来讲,每月一万元的融合费用已经相当低了。
作为地处城中村的村级公办园,普通儿童在这里上学,一个月只需要250元钱。因此,这一万元的融合费用,并不意味着幼儿园能够“赚到钱”。
图12 普通儿童的收费公示
除了学费,幼儿园几乎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他们也开始探索通过其他方式增加收入,例如举办公益活动创收等等。
山西忻州星星屿创始人彭帅臣也坦言,“都是家长一步一步做起来的,根本没指望靠这个挣钱,说实话也并没有什么盈利”。
周婷婷用私立牙科诊所来比喻融合教育,符合市场价格才能换来更好的服务,孤独症儿童融合教育亦是如此,更好的融合效果就意味着更多的时间与金钱的投入,这不可避免使得融合教育的成本居高不下,许多家长在寻求高质量融合教育的过程中步履维艰。
在运营过程中,除了经济压力和开销成本的矛盾,群体平衡的矛盾也同样突出。
融合教育中不可忽视的绝大多数主体是普通儿童,普通儿童的家长直接影响着子女对孤独症儿童的态度,也影响着子女所在幼儿园能够接纳孤独症儿童的数量。
多位园长都多次提到了“融合教育的比例”这个关键概念。一般而言,幼儿园需要保证1:8至1:10左右的比例,即8个至10个小朋友中有一个是特需儿童,才能营造融合教育的环境。只有保证高比例的正常儿童才能为特需儿童提供一个良好的引导环境,并形成榜样示范作用,激发特需儿童的社会理解潜力和模仿能力,从而提高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情绪控制能力。
因此,普通儿童及其家长的态度是融合幼儿园能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正在为儿子寻找幼儿园的朱江,仔细地读着幼儿园门口张贴的告示。当被问及是否能够接受将自己的儿子送到特需儿童比例为10%的融合园时,她立即皱起了眉头。“如果划片入学,那没办法,有一两个不正常的孩子也行。但10%这个比例还是太高了,我还是有顾虑”。和大多数家长一样,她们愿意尊重孤独症儿童受教育的权利,但依然担心自己的孩子在与孤独症儿童相处时受到伤害。
朱江的担心不无道理。自从新三余幼儿园转型为融合幼儿园后,许多无法理解孤独症的普通家长产生了一些难以打破的固有观念,将新三余村幼儿园看作是“傻子幼儿园”,认为这些孤独症儿童会把病“传染”给他们的孩子,并对此避而远之。
安老师也处理过多次这样的矛盾。小孩子之间,磕碰一下本是常有的事儿,但“融合”似乎加剧了这些细小的摩擦,将其变得尤为敏感和尖锐。
安老师认为,可能有百分之三十左右、有情怀的家长是认同融合教育模式的,但这个前提是必须保证普通儿童不能受到伤害。“所以,做这一块的教育我很小心,非常非常小心”。她提到,在招生时,也对孤独症儿童的情况设置了一个基础标准,比如“不能打人骂人,也不能伤害自己”,并时刻关注着孩子的情绪,一旦有状态波动,就会暂时切断他的社交连接。
因此,星愿教育实际上并不敢拿着“融合教育”的牌子去招生,而是选择将其置于一个较为模糊的灰色地带,以更谨慎和细致的方式与家长进行沟通和解释。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连宁对此表示,实际上,幼儿园在实践过程中不需要把这个影响看得这么大,残疾人教育有回归社会主流的理念,并不能把他们割裂开来,这并不会对其他孩子有什么损害,也不会涉及到侵犯他人权益。
此外,近年来出生率不断降低,但孤独症的患病率却在持续上升,如果无法达到融合的比例,融合教育的未来也或许会面临新的困境。
桃源内外逐渐清晰的未来
下午的自由活动结束,小朋友们手拉手,排成排,走进教学楼。他们的脸蛋被太阳晒得红扑扑的,眼睛亮亮地看着老师,待老师一声令下,便整齐地蹲下,脱下自己的外套,“左右小门关一关、两只小手抱一抱、我们一起弯弯腰、我的衣服叠叠好”,叠好自己的衣服,再放进小柜子里。
第一个进教室坐好的,可以获得一张小卡片作为奖励。小朋友们蜂拥进了教室,很快,喧闹的走廊安静了下来,只剩下了孤独症儿童沐辰一个人。
他慢慢地蹲下,重复着别的小朋友的动作。
图13 其他小朋友已经离开,沐辰在队伍的最后叠衣服
他也许早就已经忘记了,在妈妈带他叩开幼儿园大门时那些叔叔阿姨摇头的样子,也不知道在遥不可及的未来,自己能走向哪里。视线范围内,只有那件需要叠好的蓝色外套,慢慢地,抚平、捋顺、折好。
在这几分钟里,没有老师在一旁辅助、催促,没有别的小朋友嬉笑打趣,他没有被另眼相待,像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孩子一样,被等待,被接纳。
夜幕降临。
美术老师正拿着颜料,在墙上涂涂画画。他说:“孩子们自由活动的时候在墙上七七八八画了点,我把他们零散的笔画融合起来,让画更加完整丰富”。
桃源里,融合教育的意义真正显现。
而桃源外,更多的人试图为他们勾勒一个更加清晰的未来。
河南省的奇色花幼儿园,逐渐探索向教育公益组织转型的路径,不断发展为规模化支持融合教育发展的科研实训中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北京大学合作,在山西省妇幼保健协会等单位的支持下,在山西太原开设了融合教育项目基地……如今,融合幼儿园渐成规模,也有了完整科学的体系,并向外延展,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国务院原参事汤敏提到,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也开始探索融合教育新的路径。
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那些行业的初探者,开始尝试着延伸这条融合教育的道路。
孤独症儿童果果的爸爸是北京市朝阳区融合站的站长,也是最早一批推动融合教育逐渐成型的中坚力量。
与其他家长不同的是,他没有走“自立门户”创立融合幼儿园的道路,因为他知道,孩子要长大,漫漫求学路、乃至融入社会的每个阶段,如何被融合、被接纳,才是孤独症群体最根源的议题。正如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连宁所言,“特需儿童群体的融合教育现在是我们国家一个薄弱项,算得上是一个盲区”。
于是,果果爸成立了朝阳区融合站,开始了“自下而上”的探索之路。这条路,他一走就是六年。
他和家长们一起,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先是发起意见征求、广泛收集关于融合教育五花八门的建议,再集中讨论诉求,将诉求写下来,形成一个议案初稿,然后联系研究特殊教育的人大代表,希望他们能够将融合教育的需求加入到自己的提案当中,反映上去。
图14 家长们向人大代表提案的草稿建议
每一年的侧重点都有所不同,他们尽量将诉求落到实处,例如上图提到的学费问题、环境建设问题等具体环节,并且深挖融合教育难以广泛推开的原因,从根源入手。北京市教委也会针对他们的需求进行回复,由此形成了一条畅通的路径。
图15 北京市教委回复文件的部分截图
果果爸记得,六七年前北京市拨款为特需儿童设立了资源教室,但效果甚微,最终成为了摆设,他们深入调研,抽丝剥茧,发现:有了场地,但没人——核心是融合教师资源的问题。
顺着这个思路,家长们将那一年的诉求落实于“希望学校为特教老师、融合老师增加编制,从而扩大教师资源”,从北京市教育部门、到国家编制委员会,他们一步步深挖下去。挖到最后,他们发现国家现在处于缺编的情况,教育部门也正在编制改革当中,发现这条路走不通,“没关系,那就找下一条”。
一年一年走下去,果果爸和家长们确实闯出来了一条道——就是在更高年级的融合教育中,让“陪读老师入校”,辅助孩子融入正常的环境中,在必要时撤出。
2020年《关于加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发布,《指导意见》明确完善随班就读资源支持体系,允许陪读老师入校。
从政策发布到具体落实,家长们有了切实的感受。“这几年开始,北京所有的区都在推进,朝阳几乎没几个学校不能接纳我们的孩子了”。
没有消极抵抗、没有怨天尤人。他们广泛地学习政策、法律知识,在社会体系中寻找最高效、有效的方式向上触达,找空白、填空白,为自己的孩子争取最大的权益,也为特殊教育这个数量庞大、却不那么被看到的群体开辟新的路径。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连宁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很多孤独症等特需儿童连接受教育、融入集体的机会都没有,而一旦他们错过了这个时间点,其终身的发展都将受到严重制约。虽然部分民办学校可以提供教育,但收费高昂。所以,不仅是从融合教育事业发展的角度,更要从保障权益的角度出发,国家相关部门要在残疾学校里增加融合教育的内容,要加大投入,要健全机构。
落实到政策层面上,融合教育也逐渐呈现出清晰的发展脉络。
图16 关于融合教育的政策脉络梳理
此前,我国关于融合教育的政策发展主要位初探阶段,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整体进程仍然缓慢,聚焦于“普及”和“提质”两方面,主要依靠民间力量推动。二十大以后,融合教育迎来了转折点。
2022年,教育部等多部门联合制定了《“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积极促进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融合,探索融合教育模式。这一举措,标志着“融合教育”从民间自发推动正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
2024年11月,最新修订的《学前教育法》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要根据辖区内残疾儿童数量、分布特征、类型,统筹开展学前特殊教育,并推进融合教育实践体系,为相关政策的落地提供了法律依据。
从宏观政策落实到省市、乃至个人层面上,“最后一公里”被打通,改变也逐渐明朗。
彭帅臣说,之前,孤独症群体最大的难题是没有幼儿园可上,就算有了幼儿园又没有钱可上,很多家庭无力承担机构和幼儿园的融合费用,这也是他自己开办星星屿融合园的最初原因。
他提到,近年来,相关部门加大对特殊群体的补贴力度,给孤独症0-6岁的孩子发放补贴,北京发放三万六千元补贴,江苏发放四万元,山西省一年补助一万六千元,补贴区域覆盖全国范围。彭帅臣建议家长们将这些国家补助直接用于抵扣学费,从而减轻了融合的经济压力。“每一年想进入幼儿园的孤独症儿童数量都在上涨,我们这排队都要排到后年去了”。对他们来说,融合教育再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从融合幼儿园出来后呢?接受过融合教育的孩子是否更能融入社会,是否能够接受正常的教育?
安老师统计了近些年孩子们的去向,随着融合教育数量和质量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孩子能够继续升学,而不是像之前那样,在家待着,一待就是几十年。
没错,那些连吃饭、冲厕所、走路都成问题的孩子们,可以上小学了。
而那些最初的融合教育入局者,也已经伴随着行业发展走过了十几个年头。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移至当下,看看当时那些被幼儿园拒之门外的孩子们,现在的样子。
最初,促使安老师进入融合教育领域的孤独症小男孩已经成年了。他与安老师已经建立起了难以分割的情感连结,常居住在安老师家里。得益于长时段的融合,他能够进行简单的日常社交、也有了良好的自理能力,能够独自去做家务、去理发店剪头发。
周婷婷的侄子融合干预了6年后,缓冲了2年,正常升入到了普通小学,现在学习和融合状况较为理想。
彭帅臣在女儿幼儿园毕业后,他将自己的业务又扩展到大龄孤独症青年,创办了适合他们的融合教育班,让女儿和年龄相仿的孩子继续接受针对性教育。
从融合幼儿园毕业后,果果也顺利升入了普通小学。现在,她是一名四年级的小学生。3-6岁的融合提高了她的自理能力,也有效提高了她的社交能力。如今,她能够像一个正常孩子一样,遵从集体指令、排队去食堂打饭、认真听课学习。
果果爸爸站在融合领域的最前沿,伴随着女儿的成长,一步一步推动着融合教育的发展,从幼儿园、到小学,他们以群体的力量逆推着教育改革和进程,他讲到,未来,还想尝试让初中、高中或者高职等学校都能够容纳孤独症孩子。
果果爸爸笑着说,现在,他的烦恼再也不是孩子没有学上,被学校拒之门外、被社会隔离开来。
而是——“今晚又要辅导女儿做数学题了”。
那些被幼儿园拒收的小朋友们长大了,融合教育的大门也越开越大了。
(文中小付、小柴、丞丞、沐辰、果果、道道、安吉为化名)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十六颗西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