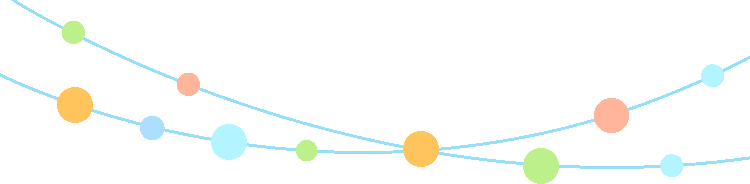日本东京大学教育学部佐藤学教授,系教育学博士,长期专攻课程论、教师学。著有《美国课程改造史》、《教育方法学》、《教学研究入门》、《课程论评》、《教师这一难题――走向反思性实践》、《设计教育改革》等等。笔者同他有20多年的交往。本文归纳了新近几次我们交谈的内容。
 教学范式的转换
钟启泉:日本文部省借助1989年《学习指导要领》的修订,着力倡导“新学力观”,似乎有种种的说法。您是怎么理解的?
佐藤学:可以说这是一种打破“应试学力”――偏重“知识、理解”的死记硬背、在试卷上写出所记忆的“正答”――的学力观;一种重视每一个学生的“兴趣、爱好、动机、态度”并求得“兴趣、动机、态度”与“知识、理解”的均衡学力观。这种新学力观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重视创造力的发展。
钟启泉:不错,一味强调学生作出“知识、理解”的“正答”的死记硬背,可以说是追求千篇一律的“标准答案”,难以培育发现、创造新的独特的“正答”的创造力。学生的“兴趣、爱好、态度”自然就难以得到尊重。
佐藤学:所以,“新学力观”是重视每一个学生的“个性”、“自主性”、“主体性”,旨在培育每一个学生的思考力、判断力、想象力、创造力的学力观;也是一种重视人际沟通,重视合作能力的学力观。“沟通能力”亦即“阅读、写作、讨论、判断、表达的能力”。
钟启泉:我知道,这个“新学力观”在日本教育界得以在一定程度上的渗透过程中,于1995年设立了第15届中央教育审议会(中教审)。中教审展望日本21世纪教育发展的理想模式,于1996年发表了第一次咨询报告,该报告书强调“留有余地”与“生存能力”。这是“新学力观”的进一步发展吧?
佐藤学:是的。根据文部省的解释,所谓“生存能力”是指“自己发现课题、自己学习课题、自己思考课题,主体地作出判断、行动、更好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律,团结,温情脉脉的丰富的人性和坚韧不拔地生存的康与体力”;是指智、德、体的和谐发展。这也是“兴趣、爱好、态度”与“知识、理解”的均衡问题。“生存能力”或是“新学力观”的提出可以说是“学力”概念的基本框架(范式),给日本教育界带来了学力观的范式转换。
战后日本的学校教育以“学力”概念为中心展开了一整套的话语系统:“学力低下论”、“基础学力论”、“应试学力论”、“鲜活学力论”、“丰富学力论”、“新学力论”等等,而学校的“教学”是同这些“学力论”密切相关的。通过教学儿童应当形成怎样的学力呢?这是教学的中心问题。因此,“学力观的范式转换”必然要求“教学(观)的范式转换”,这意味着,转换对于教学的基本认识的框架,同时也转换教学(实践)本身。通过教学的转换,儿童的学力也得到改变。
 从“传递中心教学”到“对话中心教学”的转换
钟启泉:“新学力观”寻求“教学范式的转换”。它抨击传统的、构成日本学校教育之主流的教学――“传递中心教学”。据说,这是明治(1872)年即日本的义务教育开始以来,乃至战后50年来一直沿袭的教学方式。那么,何谓“传递中心教学”?
佐藤学:所谓“传递中心教学”就是指教师向学生片面地传递“制度化知识”的教学。“制度化知识”具有如下四种性质:①这种知识是在现有的被视为学问(科学技术与艺术)、作为真理与真实的知识中经过政府检定(或是国定)的,某种意义上说是经过过滤的知识。②这种知识是儿童“能够理解和传递”、亦即被转换、归纳成得以传递的话语(文字)这样一种制度(约定俗成)的知识。③这种知识在大多数场合是在当代的学问中显而易见的结论(正答)。亦即无须儿童通过学术论辩就可以学得的,而不过是通过检定教科书的学习,学习被视为“正答”的结论。即便要经过论辩的场合,也仅仅是学习有若干结论(正答)的知识。④这种知识由于是局限于上述框架里,教师、家长和儿童也没有感到必须超越这种框架去求得知识。
钟启泉:在这种教学中,教师是借助儿童记忆了多少支离破碎的知识来加以评价的。所谓“接受教育”无非就是在学校、在私塾、在家庭,灌输“制度化知识”。所以,倘若儿童在共同的知识框架中学得比别人多一点,就可以在应试竞争中取胜。无论日本还是中国,私塾或是补习学校所以长盛不衰,根本原由恐怕就在于此。您能不能进一步阐述一下“传递中心教学”的特征呢?
佐藤学:“传递中心教学”的问题在于:第一,把儿童视为被动接受知识的存在,视为一张白纸,一种容器。片面灌输知识的结果是,儿童原本拥有的主观能动性也被消磨殆尽。第二,使儿童丧失了学习的本来目的。学习的使命仅仅归结为记忆现成知识,在应试竞争中出人头地。
“传递中心教学”亦即“一问一答式教学”、“教师主导型教学”。流程一般是,教师(T)→学生(P)→T→P→T→P。在这里,是学生(P)针对教师(T)的提问作答的循环往复。可以说是一问一答式的。而且,提问一般是期待一种答案(正答的范围狭窄),也是一种“收敛型提问”。这种教学也叫“教师主导型教学”。无论教学的过程,还是教学的结果(正答)都握在教师手里,由教师向学生传递、评定“正答”。
钟启泉:日本自明治5年(1872年)的《学制》以来,在全国各地推广“同步教学法”在检定教科书、国定教科书制度之下更加强化。通过明治20年引进赫尔巴特学派的“五段教学法”,这种教学法定型化了。直至战后所谓的“导入、展开、总结”的“三段教学法”,这就是日本“传递中心教学”形成、发展的基本线索吧?形成“传递中心教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可能在于教学目标与评价的单一化、凝固化。借助一次或数次的考试评定学生是否实现了同一目标,势必使得每一个日本学生都被按同一尺度甄别和排队。
佐藤学:不过,教师借助一次或是数次的定期考试甄别学生的做法是非教育性的,也叫“总结性评价”。另一种不同的评价是“形成性评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同“掌握学习”(mastery learning)联动的。在日本,它成为“人人得满分”教学的有力工具。具体来说,为使学生达到一定的教学目标,在途中设定若干中间到达目标,在确认学生达到了中间到达目标(形成性评价)之后,视每一个学生的实际情形展开指导。所以,这种评价也是目标与评价的一体化。
钟启泉:针对教师的提问,学生作出多样回答的教学也是存在的。那么,按照您的逻辑,这种教学的流程一般是T→P→P→P→P→T→P→P→P→P→P→P了。这是“一问多答式教学”,教师的提问期待多样答案,可以说是“发散型提问”。一般说来,“发散型提问”展开的亦即“一问多答式教学”。
佐藤学:这里,教师并不是向所有学生传递既定的同一的“正答”,学生也要创造“正答”。所以,也称为“儿童主导型教学”。这种教学在日本战前的“大正自由主义教育”(新教育)中有所体现,在战后“新教育”的潮流中作为“儿童中心主义”、“创造性开发”的策略而成为主流。后来被批判为“低学力论”,在强调“科学与教育”的呼声中跌下主流宝座。确实,这种教学过分听凭学生,习得的知识和概念模棱两可,教学过程(秩序)往往失控且难以求得每个学生的发展,“好生”风光十足,“差生”却得不到教师及时指导。
钟启泉:倘若把“一问一答式教学”的流程(T→P→T→P)与“一问多答式教学”的流程(T→P→P→P→P→P)合成起来,就成为(T→P→P→P→P→P→T→P→T→P→P→P→T→P→P→T)的流程了。在这种场合,扩散型提问与收敛型提问兼用的居多。教师的作用是梳理、引导学生的议论。教师和学生一起探讨真理、探讨“正答”,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种“师生共同探究型教学”。
佐藤学:可以说,这就是“对话中心教学”。在教师与学生借助反反覆覆的对话,一起探究和发现“真理”的过程里,重要的是每个学生的“为什么”、“怎么样”的疑问和挫折、错误、发现。每个学生的发言都受到教师的引导,在彼此的对话中,探究“真理”。在“对话中心教学”中,调查、实验、活动、制作、栽培、饲养以及其他直接性体验学习受到重视。亦即,这是一种鼓励每个学生动员自己的五官,能动地作用于客观世界的教学。当今日本的课程与教学的改革,说到底,就是实现从“传递中心教学”向“对话中心教学”的转换。
“对话中心教学”的基本原理
钟启泉:谈到“对话中心教学”,自然想到著名的巴西教育学者保罗•弗莱雷(P.Freire)的名著《被压迫者的教育学》。该书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讨论了“对话与对话教学”的问题。
佐藤学:是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把教育的本质理解为“自由的实践”。他猛烈抨击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倡导“对话式教学”。他说,“对话是人与人的接触,以世界为中介,旨在命名世界”。“这种对话不能简化为一个人向另一个人‘灌输’思想的行为,不应当成为一个人控制另一个人的狡猾手段,而应当是一种创造性行为。”保罗•弗莱雷强调说,缺乏对世界、对人的挚爱,对话就不复存在。爱意味着对别人的责任。爱是对话的基础,也是对话本身。
钟启泉:没有谦虚的态度也不可能进行对话。保罗•弗莱雷说,对话双方倘若缺乏谦逊,对话就会破裂。如果总以为别人无知识而不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如果自以为高人一等,自己是知识与真理的拥有者;如果对别人的贡献不闻不问、甚至感到被冒犯;如果担心自己被别人取代……那么怎么对话?――这一连串的设问,对于打破“教师中心主义”的束缚实在是意味深长的。
佐藤学:他还强调对话需要彼此信任。信任是对话的先决要求。倘若我们的教学浸润在挚爱、谦逊和信任的氛围之中,对话就变成了平等的对话,这是同灌输式教学中的“反对话关系”形成对照的。此外,他提出了对话双方必须拥有希望,必须进行批判性思维。上述这些,可以视为我们建构新型教学规范的基本原理。
钟启泉:让我们好好记住他的一句话:“没有了对话,就没有了交流,也就没有真正的教育”。
var cpro_id = “u2085020”;